我們對快手的想象,
是否過于狹窄與扁平化了?
被定義的快手
快手,當前直播領域的頭部平台,從宣傳語“記錄世界,記錄你”不難看出其定位——記錄每個普通人的生活。
一個事實是,許多人對快手始終存在“低端”的刻闆印象。
刻闆印象的形成源自個體的直接經驗、人際溝通、群體交流, 特别是各種媒介對認知客體的全方位塑造。
由于“快手”的技術邏輯是将流量賦予普通大衆,構建“再中心化”的傳播生态,因此視頻水平不免參差不齊。當大量生活片段毫無保留、不加修飾的呈現在你面前,我們恐怕很難感受到美感,個人經驗推動了群體傳播,進而引發輿論的發酵,再加上快手在媒體上的形象往往并不高端……因此,它被大衆貼上了“土、低端”的标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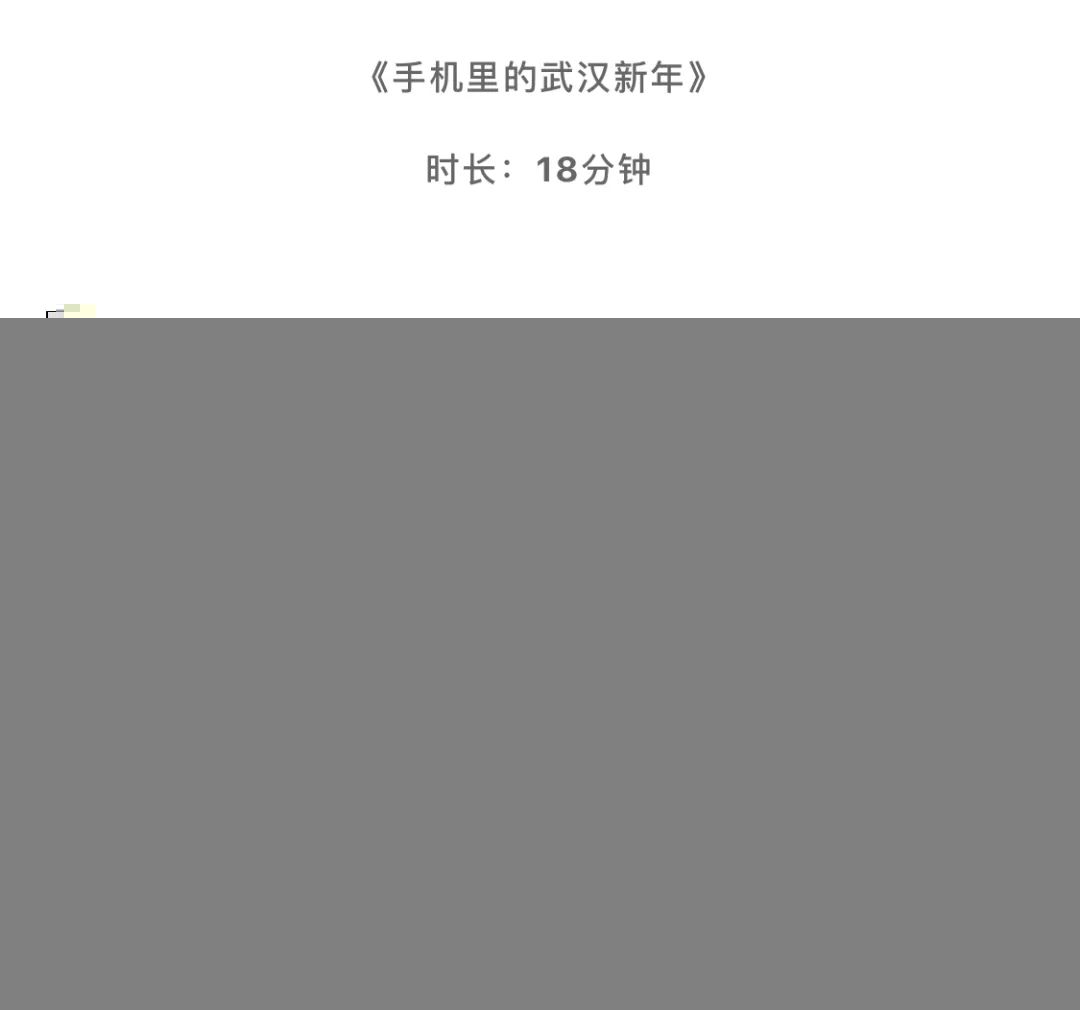
可就是這樣一個飽受诟病的平台,卻為公益紀錄片和線上音樂會提供了野蠻生長的土壤,實現了一次與藝術與影像的聯結。
手機影像中的武漢
4月2日,清華大學清影工作室發布了一則公益紀錄片——《手機裡的武漢新年》。這條時長18分鐘的抗“疫”紀錄片,素材全部取自快手,77位作者與112條手機短視頻的背後,是每個武漢普通人的視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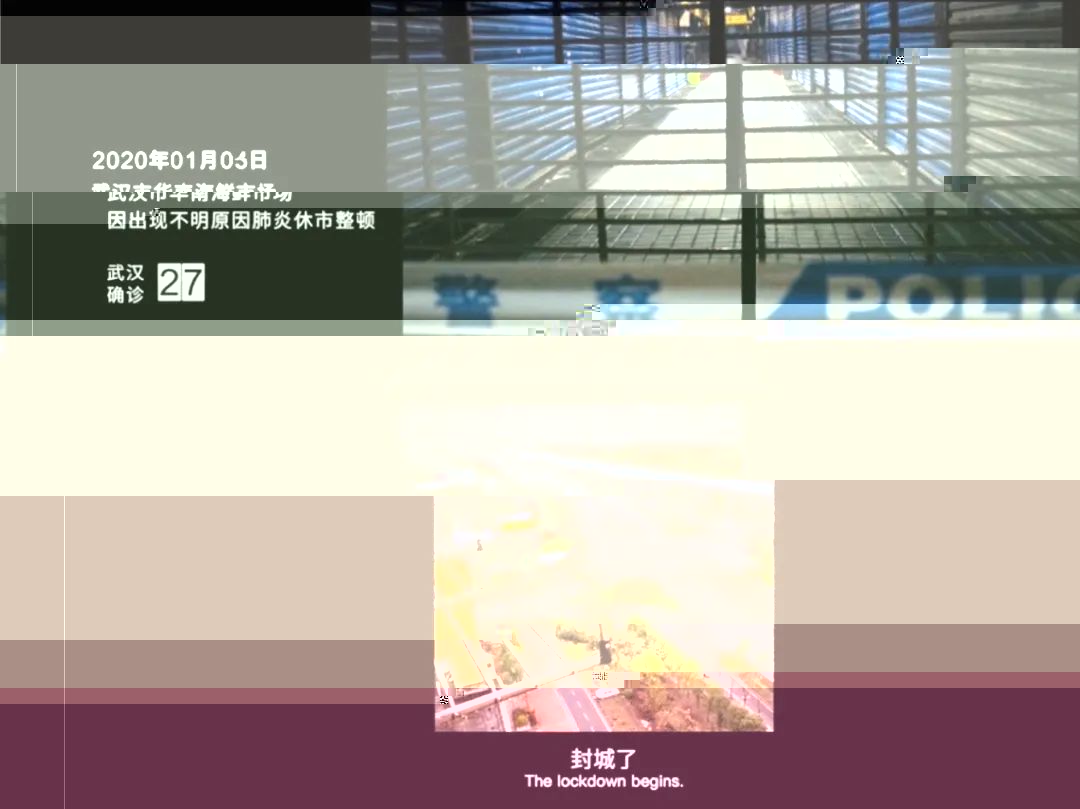
紀錄片視頻截圖
這些手機紀實影像或許在大衆看來,是粗粝的、不專業的,甚至是不美觀的,但卻真切地反映了疫情期間人們與城市的狀态。
一條短視頻或許隻會被淹沒在互聯網中,但當無數普通人拿起手機,用鏡頭記錄下當前的視角,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便在電光火石間完成了。正如主創所說,“這些手機影像的打動力,無關畫質、無關技術,隻關乎于心。”這些UGC影像從某種程度上為我們拼湊起了一個真實且立體的武漢,因而彌足珍貴。
給藝術加點煙火氣
4月26日,第二期UCCA快手良樂音樂會結束。
與以往音樂會不同的是,這次活動是由UCCA進行策劃,依托快手這個平台,邀請數位音樂人用“跨時空音樂接力”的方式進行對話,傳播藝術。
藝術對很多人來說或許是一個朝聖的對象,與“快手”有天然的抽離感。因此,當兩者相遇的時候,我們不免産生疑問:當快手這顆石子投入音樂大海時,會激蕩出怎樣的水花?


坂本龍一的快手直播現場
結局是出人意料的,從第一期坂本龍一的自然之音到第二期的先鋒電子實驗,這場線上音樂會吸引了數百萬觀衆。
快手作為當下正炙手可熱的新媒體平台,受衆自然十分可觀,再加上平台本身過硬的專業技術,讓受衆與策劃者的訴求都可以得到滿足,因而促成了UCCA快手良樂音樂會的成功。
當我們身處快手平台進行藝術欣賞時,朝聖的動作好像消失了,或者說不再像往常那麼明顯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的“毫無違和感”的驚奇感和“我也可以欣賞藝術”的親切感。它不僅僅為我們提供了一場音樂盛宴,還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我們的刻闆印象。它讓我們知道:藝術并不是高高在上的,以快手為代表的衆多短視頻平台也不應該被标簽禁锢——我們應該看到它們的另一面。
正如策劃人尤洋所說:“它不僅不會失去藝術最核心的光暈,反而會在藝術表達和連接公衆上展現出新的魅力。”藝術借力快手平台,在為更多人提供觀賞機會的同時,也給看似遙不可及的藝術增添了幾分煙火氣。
看到更多的可能性
這部紀錄片和音樂會無疑抛給我們一個問題——我們對快手的想象,是否過于狹窄與扁平化了?
其實,這三者都不該被定義。假如都被我們的想象綁架、失語,讓刻闆印象吞噬掉它們所有的一切,我們不知道會失去多少個18分鐘的感動與幾小時的歡愉。
我們要記得,無論是音樂、影像還是短視頻平台,他們都有無數個切面,正因為這些切面的存在,才讓我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。
參考文章:
SocialBeta《坂本龍一在快手的直播紅了,我們和促成這件事兒的UCCA Lab聊了聊》
南方周末《專訪坂本龍一:“對于自己的脆弱,我希望能夠時常保持坦率”》
毛偉《短視頻新視域下發展傳播學的中國範式》
周大勇《重塑東北形象:刻闆印象的轉變與積極傳播》
作者/趙舒翼
指導教師/徐藝心
輪值主編/吳垠
責任編輯/黃怡靜